《普鲁斯特与符号》(第二部分:文学机器)
分卷缩写如下:
CG — 盖尔芒特家那边;TR — 重现的时光;AD — 女逃亡者;JF — 在少女们身旁;CS — 在斯万家那边
和之前一样,粗体和斜体是重点和高能部分,【 】里是自己的批注,( ) 标注中译本页数。写笔记过程中批注和个人理解的区别不是很明晰,所以括号外个人想法的含量也很高,请注意辨别。
第二部分:文学机器
8. 反逻各斯
《追忆》中有许多朋友、哲学家、观察者、知识分子一类的角色,他们虽然身份不同,却都分享着逻各斯,也就是不断编织整体到部分、部分到整体之间的关联,一种对总体化的偏爱。(103-104) 在逻各斯中,人们只能获知已经提前知道的东西。和逻各斯的观察、哲学、反思、按逻辑和一致地使用官能相对立,《追忆》提出了感性、思想、翻译、非逻辑和断裂地使用官能。(104-105) 也就是说,1. 我们不能同时支配所有官能;2. 理智总是延迟到来。(105) 普鲁斯特用符号和象征来反对属性,用帕索斯 pathos (接近于情感的力量)反对逻各斯 logos。(106)
符号和逻各斯的对立由五个方面构成:1. 所划分的那部分世界;2. 揭示的法则;3. 官能的用法;4. 统一性的类型(符号的统一,还有逻各斯的统一,分别意味着什么?);5. 对其进行解释的语言的结构(风格)。(107)
普鲁斯特身上有柏拉图主义的影子,体现在他关注“记忆和本质”。柏拉图认为灵魂对各种符号进行解释,从而进行回忆,从中发现本质。然而,正如前文结尾所言,他们的差异体现在:柏拉图认为各种生成变化都是世界的某种状态;回忆的终点是理念,是稳固的本质,是一种被注视和见证的客观性,在最开始时已经形成了,回忆并没有造成新的东西,仅仅是“寻回”。(107) 而在《追忆》中,生成变化仅仅是某个灵魂的状态,总是处于主观联想之中;回忆的终点则是一个更高的视点,而不是某种被看到的东西。(108) 这意味着,在回忆的终点,我们达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起点,是诞生而不是寻回。
在现代文学中,世界的秩序不再,变成了碎片和混沌,因此需要设想一种现代化的客观性和统一性。这种客观性只能存在于艺术作品那富有意义 (signifiante, 正在指意) 的形式性结构,也就是风格中。只有在这里,主观联想的链条才能断裂,跳出被构成的个体,转化为生成个体的 (individuant) 世界的诞生。再回忆,就是创造出回忆在精神上的等价物,创造出对所有联想【主观联想】都适用的链条,对所有形象都适用的风格。风格以人们谈论经验的方式和表达经验的模式 (formule,套路,还有专业用语的意思) 取代了经验,用对世界的视点取代了世界中的个体。 (109)【对世界的视点是非个体的,我的理解是,个体是一堆视点的综合,例如我们所处的环境、具有的知识、感知模式、情绪状态、人际关系,每个方面都会发展出对应的表达经验的方式。】
希腊世界的符号:《斐德罗篇》、《会饮篇》和《斐多篇》对应了狂热 (délire)、爱和死。希腊也有碎片式的箴言、神谕、疯狂,但希腊精神中符号是不完备和欺骗性的体系,必须通过辩证法修复成完整的逻各斯。(110) 部分、碎片和符号有两种形成的方式:1. 预设了那个它应该归属的总体,就像一个小宇宙 (microcosme),部分反映出总体,并据此连接组织在一起;(111) 2. 让不属于同一个整体、不能匹配、不能沟通、有不同尺度和形式的片段为自身言说,不再依赖于持存的逻各斯:只有艺术作品的形式性的结构才能对这些碎片性的质料进行破解,并且不借助外在的指涉、讽喻或类比的框架。普鲁斯特式的回忆不整合,不是同感 (synpathie),而是信使,既不与传送的信息匹配,也不与收信者匹配(译注:好像在说信使 DNA),例如夏多布里昂说“纽芬兰狂野的风”而不是故国的微风带来天荠菜的芳香。一种现代性的记忆概念:一个异质性的联想序列,只能由一个异质的创造性的点来聚合,这样才确保了偶然的纯粹性,阻止理智提前到来。(112) 艺术品不是一个有机的总体。例如,《追忆》中维梅尔的画作价值不在整体,而在于那块黄色的墙壁,它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碎片。【这也是德勒兹所谓“普鲁斯特的植物性”的含义——随便掰一根枝条插到地里,它能发育成一棵单独的植物。艺术品也具有植物的这种自分形特征,而不是有性繁殖的动物。】这本著作中的碎片每个都指向不同的整体,或不指向任何整体,或不指向除了风格整体之外的其他整体。(113)
9. 箱子与瓶子 (Les boîtes et les vases)
《追忆》各部分间存在着不一致性、不可公度性、碎片性。这里有两个形象,一个关乎容器-内容,一个涉及部分-整体的关系。前者是嵌合、包含、蕴含 (emboîtement,成盒),人们从一种物或名字中获得具有另一种性质的事物,就像主人公试图从石板路中挖掘出威尼斯;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需要解释、展开、展现那些内容。后者是复杂性 (complication),即不共通的部分并存,例如相互对立的两边;对此,叙述者需要选择。(114-115)
第一种形象是半开的箱子,第二种是封闭的瓶子。(115)【搞不懂!】第一种的价值在于缺乏共同尺度,第二种则在于和不共通的相邻者对立。这两个形象也会不断相互融合。比如,阿尔贝蒂娜既复合 (compliquer) 了很多不同的少女,又蕴含 (impliquer) 了海滩和浪潮的印象。前者,在不同的环境和欲望下,我们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而后者需要我们去阐释和展开。【关于 complication 和 implication,之前已经讲过,前者“折叠在一起”,像两张叠在一起被揉皱的纸;后者“内部折叠着”,像手风琴的风箱,可以一开一合。不过还是没搞明白 vessel/vase 为什么对应 complication,难道这里取 vessel 管道的意思吗?也不太对啊……】(116)
从官能的角度:无意识记忆打开箱子,展现其内容;欲望或睡眠则旋转封闭的瓶子,从中选择那个最好的、最适宜当前情况的侧面。从爱情的角度:欲望致力于增加爱人的不可共通的形象【不断迭代对爱人本人的建模】,记忆则从 ta 身上刨取那些不可公度的印象【风景】。(116-117)
什么是容器?内容包括什么?容器和内容的关联是什么?什么是解释?解释在容器和内容的抵挡下遇到了什么困难?真正的容器不是日本纸花绽开的小碗,而是感觉属性;内容也不是由此出现的联想链条,而是本质和纯粹视点。视点高于由它看来是真实的东西。【普鲁斯特对贡布雷的描述方法高于被描述的细节本身?】事实上,内容已经被完全遗失,永不会被拥有,以至于对它的重新获得就是一种创造。本质不仅唤起那个体验过这些联想的自我,还让我们体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存在。所有对某物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复活某个自我。(118)
被爱者就像感觉属性,价值在于所包含的东西。【虎狼之词,but i agree】爱人对我们来说,表现了一个或一些可能世界。一个存在者的内容,就是 ta 的表现性 (expressivité)。但内容和容器之间不只有一种联想的关联【主观性】,还有一种奇妙的“扭力”,把我们置于被爱者所表现的未知世界中,让我们脱离自身在另一个宇宙中呼吸【应该是指爱情的强力驱迫。有时候沉迷某作品、艺术家,也会有种离开生活去他们的世界旅游的感觉】。(118-119) 在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中,叙述者的联想链条被掐断,他被置于爱人所表现的风景中,仅仅是为了从中被排除和驱逐,而且这次断裂也没能带来本质的呈现,而是由一种清空 (vidage) 的运作形成。“清空”把叙述者还给了他自身,因为他想把被爱者囚禁起来,以便更好地解释她,“清空”她身上的世界。结果是,“只有嫉妒能在她身上瞬间产生一个宇宙,而一种缓慢的解释则努力将其清空”。【我觉得这段非常好地描述了一些坠入爱河和被圈粉的过程——我们发现自己掉进一个陌生的世界,痴迷,回不了头。为了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拼命分析,而被爱者在这种分析中渐渐褪色。然后我们才解脱。】(119) 在这么做的同时,也清空了每个爱恋着的自我。但这些自我始终挣扎着,寻求在其他事物中复生。(120)
于是,第一种容器——箱子的内容时而被清空,时而被分离(就像名不副实的盖尔芒特的姓氏),这是因为给了它最低限度一致性的联想链条也会断裂。(120) 容器和内容都爆裂了,变成彼此争斗的异质性的真理。即使是过去在本质中重临时,那个过去和当下的时刻之间也并不和谐,更像一场战争。反正,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说明这些碎片根本不构成整体。但普鲁斯特想了个办法,让我们可以思索全部片段却不需要参照【前在的】或构想【潜在的】任何整体。(121-122)
第二种形象,封闭的瓶子,它标志着相邻的不共通的部分之间的对立。例如《追忆》的“梅塞格利丝那边”和“盖尔芒特那边”,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即使是重现的时间也不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而只能增加联系、连接的路线。(TR2, III, 1029) (122) 人的面容也有至少两个不对称的方面,就像两条决不共通的相对的道路。例如女演员拉塞尔,一方面是从极近处看到的模糊一团(她的长相、品性、出身都不太行,老折磨圣卢),另一方面则是从一个合适的距离看到的精妙结构(具有超凡的表演天分)。阿尔贝蒂娜身上则是回应信任和抵抗猜忌的两张脸。这些方面分裂成千百个封闭的瓶子。【啊?为什么??什么意思???】这里举了个叙述者亲吻阿尔贝蒂娜面颊的例子,说在亲的过程中像从一个平面跃向另一个,途中经过了十个相互隔绝的阿尔贝蒂娜,最后它们都层层瓦解,而每个瓶子里都有一个自我在体验、感知、醒来和睡去。对应于爱人的碎裂和分裂,瓶子里的自我也在增殖。(122-123)
“世界”之间也这样彼此隔绝,语言也呈现出这样的分布,解释者从中辨认出各种层次和借用,体现出说话者的交际、环境和隐秘世界,比如叙述者发现阿尔贝蒂娜开始用一些新的词汇,就据此推测她进入了新年龄段、新交际网;她用的令人讨厌的词汇则展现出一个讨厌的世界【比如某些网络用语】。词语是世界的碎片,反映出说话者到过哪个区域/地层。(124)
封闭的部分之间不断彼此联络,从而形成连续和统一的幻觉,但它们之间只有联络的路线,而没有“整体”【有点像互联网】。我们在这些碎片之间旅行、跳跃,肯定它们的存在,但绝不把它们重新聚合为一体。嫉妒,是多元性的爱之间的连接路线;旅行,是多元性场所之间的连接路线;睡梦,是多元性时刻之间的连接路线。这条运动的路线肯定了两点之间的差异。(125-126)
叙述者不再展开,而是选择一个部分、选择一个瓶子和置身其中的自我、选择一个爱人的形象,然后赋予它生命令它重生。“从睡梦中醒来”就是一个选择的时刻,因为睡梦让所有封闭的瓶子和自我缓缓旋转,所有入睡之人“都在其四周萦绕着时间的游丝,年岁和世界的秩序” (《追忆》中文本(上),第 4 页);“醒来”意味着从所有的时空中选择出我们入睡的现实的房间,从所有的身份中选择出那个入睡的自我,最后摆脱睡梦的最高视点,重新发现把我们固定在现实中的联想链条。 (126-127)【妙极了,《冰与火之歌》里三眼乌鸦就进入这种状态,成为历史中的所有视点。我印象里这个设计和梦境有关系,但记忆有点模糊了。】我们不问谁在选择,因为被选择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选择一个爱人、一段体验时,实际上是那个自我被选择了。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我”?
我看不出是什么在支配着这种选择,为什么在成千上万个可能的候选人之中,偏偏就选中了昨天的我。(CG1, II, 88,中文版上卷第 602 页)
德勒兹说有一种纯粹的解释和选择,它既选择了有待解释的符号,也选择了对其进行解释的自我。解释只有贯穿的 (transversale,记住这个词,是第二部分的关键) 统一性。只有解释才是一种神明,其自身的一切都是碎片,但它的“神圣形式”只是把碎片带到最高状态,阻止它们形成整体,也不让它们彼此脱离。于是,《追忆》的主体不是自我,而是那个“我们”,即一对进行解释的符号和自我,它对众人物进行分布和选择,但不把它们总体化。(128)
这一章对符号进行了第二次分类,根据容器而不是世界的类型。符号无法被总体化,因为它的内容要么不可公度(箱子),要么不可共通(瓶子)。不可公度和不可共通性都意味着某种距离 (distance),这种距离把一物置于另一物中,或让它们相邻。【???】这里提出一种时间,它是“非空间性的距离”的系统,距离存在于相邻者或被包含者本身之中,“距离”不存在间隔。【???】消逝的时间在相邻事物间引入距离,重现的时间却在相距的事物间引入相邻性。【这段关于距离的真的不懂,怀疑和柏格森有关。】时间是最终的解释者,拥有奇妙的力量,同时肯定那些并不在空间中构成整体的碎片,但这些碎片也不因为在时间中持续而成为总体。时间是对所有可能空间的穿越 (transversale),其中也包括时间的空间。 (128-129)
10. 《追忆》的层次
【这一章的重点是法则和部分性客体】
在碎片化的世界中不存在总体性的法则,却存在另一种法则。逻各斯治下的希腊法则仅仅是在各个部分之间建立起“更好”的联系,而这个“更好”或者“善”的形象是由逻各斯规定的,因此这种法则是次要的力量。而现代性的法则是一种首要力量。法则不再言说善的东西,相反,法则所说的东西就是善。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因为它没有使我们认识任何“善”和逻各斯,并未把各部分结合在一起,而使它们彼此远离。事实上,在被法则惩罚之前,法则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法则具体是什么。 (130-131)
卡夫卡对这种法则的认知呈现出抑郁的特征,而普鲁斯特呈现出精神分裂。罪行在普鲁斯特作品中扮演的角色:首先,爱预设着被爱者的罪行。“……当我们感到被这个人所吸引并开始爱他(她)时,就意味着不管我们把他(她)说得如何纯洁无邪,我们已经看出他(她)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背叛和种种过错了。” (AD, III, 611) (132)当有罪的观念最终取代了我们对爱人清白的确信,爱也自然而然地结束了。(133)
其次,同性恋被描绘为一种受诅咒的种族,“不得不在谎言和伪誓中生存” (《追忆》下,第 916-917 页),和古希腊的同性恋相对立。(133) 这种罪行更多是社会性而非道德上的。(133-134)
普鲁斯特的整体是统计学上的整体,它分化出的两个方向也是这样,例如叙述者的一群“自我”分化成了“信任”和“猜忌”两个子群体,接着细分下去……【想想机器学习聚类算法】同样,梅塞格利丝那边和盖尔芒特那边也是统计学上的那边,因为它们自身内部也是零散的一大批形象。最后,蛾摩拉和索多玛的系列同样由器官和基本粒子的运动构成。【k-clustering 算法中,分类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你想分几类(k 的初始值),因为它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把毗邻的数据点分在一起。这一段提到“统计学”的用意应该是指出,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只是一大堆零散的部件,我们出于某些原因把它们暂看作一个整体。】(134)
两性在同一个个体上既同时存在又相互分离,相邻却不共通。雌雄同体不是指时男时女,而是像植物的雌蕊和雄蕊一样,并存但无法直接沟通。这里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异性恋的统计学的整体【最简单的顺性别者】,第二层是同性恋的统计学的整体【内在和自己生理性别相反的人】,第三层则是性倒错 (transsexuel) 【我对这个翻译非常不满意!第二部分整个在讲 transversality,一种跨越多层次的感觉,这里应该翻译成“跨性别”,下文将沿用这个译法。另外,这让我想到最近沸沸扬扬的 trans 权事件,捍卫的其实是第二层——性倒错的权利,把性别固定在变化的另一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跨”性别。】因而,它超越了个体和整体:它揭示出个体中两性碎片的共存,这些碎片被称作部分性客体 (objet partiel)【我怀疑这个和偏微分有关,单独对每个维度做微分】。(135-136) 雌雄同体需要一个第三者(昆虫)来让它的某个部分受精。这里德勒兹引入了一种微分的爱情,一种碎片性别的观念:我们的两性器官各自为政,寻觅自己的配偶,男性的部分可能寻找着男性的部分,而最后找到的对象总体上既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普鲁斯特指出,这是一种局部的同性恋。德勒兹在注释里还提到,纪德为一种同性恋-逻各斯的权利而战斗,因此责备普鲁斯特只考虑倒错和女性化的情况,这显然是没搞懂普鲁斯特的跨性别理论。【由此可以反思下当今种种平权运动,是否也致力于修建他们的“少数-逻各斯”。】(136)
【不需局限于两性器官——所有器官都可以卷进这湍流。是不是有点反俄狄浦斯的味道了?对耽美和时下流行的一些猎奇情色文学(男性产乳、受孕、双性、……各种器官的组合生产),也可以用微观性别的思维加以观察,而不是像僵化的网文论坛主持人一样炒亚文化历史的冷饭。】
嫉妒。嫉妒是符号自身的疯狂,它和同性恋有着根本的关联。被爱者包含着可能世界,而它们的价值仅仅在于被爱者对这些世界的视点。求爱者永远无法深入到这些世界中,就算他身穿迷彩潜匿在巴尔贝克海滩的沙石之中,他也只能看到被爱者在看(包括自己的)风景,而永远猜不透那个作为组织者的视点。
如果她看见了我,我对她又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相邻的星球上,某些奇怪的生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很难就此得出结论说,有人类居住在那里,他们看得见我们,看见了我们又会在他们心中唤起什么样的观念。(JF3, I, 794; 《追忆》(上),第 455 页)
嫉妒不仅仅是对可能世界的解释(在这些世界中有其他人受到爱抚的影子),而是发现了存在着不可知的世界,一片“可怕的无名的土地” (CS2, I, 276)。最后,嫉妒还揭示了被爱者的那些微观性征。对这些部分性客体的发现,要比发现敌手更残酷。(139)
监禁。监禁是从被爱者身上 1. 清空、破解、解释可能的世界;2. 它把这些世界分门别类,找到它们和被爱者之间的联结点;【举个例子比较好理解,比如被爱者是一个明星的狂热粉丝,破解就意味着搞清楚 ta 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明星,从什么时候开始,因此有哪些社交圈子,从中得到了什么,学会了什么语言……总而言之就是做一个合格的斯托卡!】3. 它切断了构成那不可知世界的同性恋系列;4. 它阻止相邻的部分性客体在昆虫的横向维度【经度?】中互相沟通。但是,在最后一项活动中,除了中断那些受诅咒的互通,它也会创造出偶然的邻近组合,向我们揭晓一些秘密。
普鲁斯特的三位一体:监禁、偷窥和亵渎。监禁是处于观看又不被看到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必冒着被别人的视点所征服的危险。观看(偷窥),意味着把别人还原成孤立的部分性客体,并等待观察那些部分重新恢复沟通的模式【也太生物实验了】。与之相对,展示,意味着迫使某人接受某种恶心异样的邻近性,【你要观察我怎么沟通,我就沟通给你看啊】还把那个人也当成客体中的一个,当成横向沟通的对象中的一个【别忘了,你也是我的一个小碎块】。而这就是亵渎的主题。(140)
亵渎。普鲁斯特写到两个带乱伦色彩的场景,一个是在母亲卧室旁亲阿尔贝蒂娜,一个是凡德伊小姐做爱时把父亲照片放在边上。叙述者还把家里的老家具卖到妓院。总之,在这些例子里,就是把父母的部分性客体连接到“不该”连接的地方,比如爱人身上,从而让他们和这个景象紧密联系起来,无法摆脱。(141)
弗洛伊德提出,对爱人的攻击性会引发两种焦虑:失去爱人的威胁,和针对自己的罪咎感。但普鲁斯特认为,罪行始终是社会的而非道德的。“失去爱人”倒确实界定了法则:去爱但不被爱。(JF3, I, 927) 爱意味着去把握爱人身上的可能世界,然而,一旦清空和解释完成,我们也就不再去爱 (JF2, I, 610-611),那个陷入爱河的自己就此死亡。另外,要把被爱者监禁起来,单方面观察,然后让他看到自己的那些分隔性场景,让他震惊。这就是监禁、偷窥和亵渎,全部爱的法则。(142)【用现在世俗推崇的“爱”的观念来看可能会难以理解,不妨理解为一种着迷现象,或者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令人痛苦的爱】
这种法则呈现于望远镜而非显微镜之下,因为它在诸碎片间安插了距离和分隔,建立起异常的沟通,强行把一个世界的碎片插入另一个世界。最微小的差异,带来的正是最遥远的维度。(142) 望远镜把普鲁斯特的三个主题集中在一起:远处看到的东西,世界之间的相撞,部分之间的相互折叠。(142-143)
他们祝贺我用‘显微镜’发现了那些真理,其实恰恰相反,我用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才隐隐瞥见一些实在很小的东西,之所以小是因为它们距此遥远,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就是在我探索伟大法则的地方人们称我是细枝末节的搜集者。(TR2, III, 1042; 《追忆》(下),第 1805 页)
“如果说痛苦是太阳,这是因为它的光芒一跃之间就跨越了间距,但却没有消除它们。”所谓相邻性,就是这样一种光的相邻性,它照耀过的距离,肯定了而非消除了间距。(143)【非常美妙。我试着解释一下“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吧。首先,它们的共同点是用来看(视觉上)很小的事物,并放大它的内部结构。然而,显微镜看到的是“基本组成结构”,它看到的毗邻性是真的毗邻,由此,可以重建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和整体性,也就是说它观察着一个可测度的区域。而望远镜看到的星球却排列在(至少是)三维空间中(还不考虑光的扭曲),两个差不多大的形象,很可能实际尺寸大相径庭;看起来近在咫尺的星球,很有可能处在银河的两个旋臂上。而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充满了不成比例、不协调的奇景和黑色幽默。】
11. 三种机器
【全程高能】
《追忆》并非仅供普鲁斯特临时使用的望远镜,它是一种供他人使用的工具。“他们不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己的读者,我的书无非是像放大镜一类的东西,……因为有了我的书,我才能为读者提供阅读自我的方法。” (TR2, III, 1033; 《追忆》(下),第 1801 页) 《追忆》也不止是工具,还是一部机器。现代艺术就是一部机器,作为机器而运转。《追忆》可以是我们所意欲的一切(德勒兹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教堂、外衣、对性别的预言、发自德雷福斯案的政治通告、各种符号和语言的密码书、社交手册、形而上学论文、……),关键是我们能将它派什么用场,从中生产出什么来。(144-146)
如果说逻各斯涉及到器官和工具 (organon),我们必须从它们与整体的关系中发现它们的意义,那么反-逻各斯就是机器装配——意义取决于功能。而功能只依赖于其零件。现代艺术作品没有意义的问题,它只有一个用法的问题。【划重点!!!】
这些机器生产真理。真理被我们从印象中挖掘出来,然后在一部作品中被呈现出来。所以,普鲁斯特反对发现真理,反对现成的逻辑的真理。【比如,格物致知。(这么看来,宋代理学追求一个“尚未到来”的总体,而明代心学则预设了事先存在的良知。)】
所有生产都始自印象,因为只有印象兼具相遇的偶然性和效果的必然性,也就是印象的强力。“想象和思想其自身可以是令人赞叹的机器,然而他们是惰性的;于是,痛苦使它们开始运转。” (TR2, III, 909) 符号开始推动一个官能,把它推到极限,解释(生产)出意义、法则或本质。意义原本和印象的“精神等价物”结合在一起,在解释工厂开工后,我们把它从千年冰川上吭哧吭哧地凿下来了。以上就是这条生产线的大致情况。(147)
【题外话,“解释”这个汉语词也有种机械感,弹簧松懈、冰雪消融(化学键松绑),解释春风无限恨。】
不存在至高至全的真理,只有真理的类别。之前,我们简单地区分出“重现时间的真理”和“消逝时间的真理”。但是,全书其实区分了三种真理类别:1. 通过回忆和本质、重现的时间的生产、自然和艺术的符号而界定的真理;2. 结合了不完备的痛苦和愉悦、从属于普遍性法则、介入消逝时间的生产、关系到社交和爱的符号的真理;3. 有关普遍的变化、死的观念、衰老疾病和死亡符号的真理。其中,第二种“辅助或承载”第一种,第三种“镶嵌或加固”了第一种,并提出了一种真正的反驳,它超越了前两种生产的类别。(148-149)
不完备的痛苦和愉悦是基本的类别。作家在其职业生涯的“见习期”熟悉社交和爱情这些原材料。这第一种机器生产的是部分性客体。所谓法则,就是把部分性客体提取出来,打破原来的整体观念,进行重组,“正如在一个浅薄的梦境之中,有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提取出肩膀的某种运动,祸从另一个人身上提取出头颈的运动,不是为了把他们总体化,而是为了使它们相互分隔。” (150)
第二种机器产生共振。首先是不自觉记忆的共振,形成于过去和现在的两个时刻之间。其次,欲望和想象也有共振的效果。最后,艺术“通过(意义相反的)词的组合这种无法形容的关联” (TR2, III, 889) 使两个原理的对象共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前一种机器为它提供了原材料(部分性客体)。只是说,它们生产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第一种机器是普遍法则,而这一种生产本质。共振抽取出的是它自身固有的碎片,并让碎片进行一次“肉搏”或“战斗”,从而生产出一个更高的视点。(151)
这两种生产过程互补而不是对立,它们各有其独特的原材料(碎片)和产品。普鲁斯特的新颖之处也不在于他写出了一两个“出神”的瞬间,因为在文学中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关键在于,他生产出了这些瞬间,它们成了这台文学机器的效应。文学的效应——就像电学、电磁效应。现在,我们在谈论文学时可以说:it works! 【it compiles! 代码工作了!不过,这说得好像普鲁斯特搞了一个现代化文学大车间。他在《驳圣伯夫》里就强调了文学效应。】在普鲁斯特这里,艺术是一种用来产生效应的机器。效应作用于他人,从此,读者开始在自身之中或之外发现这些效应。“妇女们在街上行走,和昔日的妇女截然不同,因为她们是雷诺阿的妇女,……” (CG2, II, 327; 中文版上卷第 746 页) 【雷诺阿并非发现,而是生产出这些妇女。】但更重要的,是艺术作品对自身的效应,它从自己产生的真理之中汲取营养。(152-153)
整部《追忆》在生产本质中相继摆脱了对事物的观察和主观的想象,进行了双重的否弃和纯化。与此同时,叙述者意识到,共振不仅仅生产,而且可以被艺术生产。【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机器生产机器。】(153-154)
《追忆》对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联系进行追问。艺术的作用,就是生产共振,因为风格使两个任意的客体发生共振,把无意识和自然(感觉)生产的确定条件替换为艺术生产的自由条件。【简单来说,艺术家可以选择一些客体,把它们关联起来,产生意义。而这种关联手法(风格)是受到了无意识记忆的启发。】(154)
书本就是这样一台艺术机器。艺术家和读者从客体、有含义的内容出发,把那些看似完整的形象一一解开(disentangle),使它们在碎片的增殖中瓦解,然后“再体现”(再度获得身体,这里引用了乔伊斯“神显机器”)。总之,艺术就是再组织。所指和能指通过出乎意料的短路融合在一起。于是,作品形成了新的语言学规则,并根据这种新规则成为一个总体。 (155-156)
最后,我们来看普鲁斯特的第三种机器:普遍变化和死亡的机器。最后一部中,所有熟悉的人物、景物都经历了衰老,到处是死亡的临近、世界末日和遗忘的印象。但是,在出神中,早已蕴含了一种类似的死亡的观念,例如叙述者在解鞋带的时候,死去的外祖母突然在这一瞬间中复活,本该到来的愉悦就让位给难以承受的痛苦,两个时刻不再结合,来自过去的那个时刻向外逃逸。(156) 爱情中前赴后继的自我也已经包含了一个漫长的自杀和死亡的系列。如何把这种机器和前两种协调起来?怎么处理死亡的问题?虽然记忆在纯粹的过去长存,当下却在不断消逝;这是死亡的突然呈现,如果我们不能设想出一种能从死亡的印象中产生真理的机器,文学就会遭到“最严重的的反驳”。(156-158)
死亡的观念存在于一种时间效应之中,即“当下”和回忆中“过去”的对比。这里有一种振幅【幅度?】更大的受迫运动 (mouvement forcé,也有“被迫迁移”的意思),和共振的方向相反,把两个时刻驱散、推开,把过去赶到更远的时间里,并构成一种时间的视界 (horizon)。它使时间无限膨胀,而共振使时间无限收缩。【共振把两个时刻重叠起来。我强烈怀疑这里德勒兹在暗指时间维度上的纵波——见附图。】因此,死亡的观念变成了一种混合的效应,生者、死者、半死者在巨大的时间振幅中延续着,同时触及相距甚远的几个时代,就像时间里的巨人种族。大幅受迫运动成了生产倒退效应和死亡观念的机器。时间原本不可见,但它沿路攫取了不少肉体,在它们身上显现,从而变成可感知的。对外祖母的回忆中,就是这种受迫运动抵消了共振。好了,到此,我们成功地设计了一种用死亡生产真理的机器,可以松一口气了。(158-159)【这里德勒兹说部分性客体机器 ≈ 冲动 (pulsion),共振机器 ≈ 爱若斯 (eros),受迫运动的机器 ≈ 死亡冲动 (thanatos)。(159-160) 老实说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开始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而且感觉也并不对应。懂弗洛伊德的可以讨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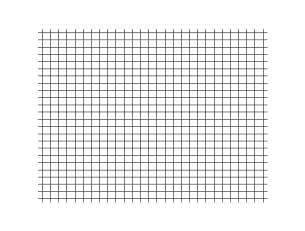
12. 风格
生产真理的机器是怎么被组织起来的?《追忆》虽然是碎片性的,却不缺少任何东西。普鲁斯特说自己的作品是一座教堂和一件外衣,这并非引入某种作为完美总体的逻各斯,而是为了行使一种未完成、修补的权利。(TR2, III, 1033-1034) (161)【想到高迪的圣家堂,到现在还没修完;还有法国邮差薛瓦勒的“理想宫”,真是一座用小石块修建的碎片化的城堡,其外观和梦境有相似之处。】本质,也没有形成总体,因为每个本质的视点都对应一个世界,既不与别的世界共通,又确认了它们之间的根本性差异。(162)
是什么让我们与一部著作“沟通”?什么构成了艺术的统一性(假如有的话)?有的,只不过,这种统一性整体不是原则,而是效应。沟通也不是原则,而是机器诸部分间游戏的结果。莱布尼兹的单子(视点)虽然表达世界的角度和重点不同,却包含着同样的内容——那是上帝放进去的同种信息,一种“先定和谐”,就像开学时所有人都拿到了同样的教辅材料。但是,在普鲁斯特那里,每一个视点都对应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统一性只存在于机器的结果和效应中。(163-164)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不存在一种先在的逻辑统一性,也没有形成这种统一性。这部著作只产生效应:“当他……猛然间发现,如果这些作品组成一个系列效果会更好,……为了衔接这些作品,他给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最后的,也是最出色的一笔。这个整体是后来才形成的,……” (PI, III, 161; 《追忆》(下),第 1298 页)而这最后的点睛之笔,改变了整个系列的本质和功能,但又没有改变这些部分的碎片性,没有把碎片整合起来,而只是位列碎片之侧。【这么看来,“点睛之笔”这个词用在此处特别合适。】(165)
风格就是对符号的解释,服务于这解释过程,而从不考虑什么整体美。(166-167) 这种解释性的风格产生如下效应:一旦有了两个客体,它就产生出部分性客体,产生共振,产生受迫运动(即前文三种机器)。风格的这些产物就是形象(意象)。这里的一段注解归纳了普鲁斯特和其他后象征主义概念如乔伊斯“神显” (epiphany),庞德的意象主义 (imagism) 和漩涡主义 (vorticism) 的共同点——文学作为生产,解释作为包含和展开的技术(而非定义),意象作为两个客体之间的关联,风格作为视点,等等。(167) 但是,风格绝不属于人,而属于本质(非-风格【non-style,感觉译作“无风格”比较好,类比于无意识】)。它并不来自一个视点,而是来自于一个语句中视点的无限系列的并存,客体根据这些视点被拆散、形成共振或增幅。【增幅也就是“受迫运动”。如果理解成纵波,那就是围绕着平衡位置振动得越来越猛,相距越来越远。至于这段中的“视点的无限系列”,可参见这篇文章中连续傅里叶变换的部分,也许理解为“客体被分解成一系列视点的叠加”会清晰一点!】(168)
风格也没有确保统一性,统一性是从别处获得的。这种体现为“点睛一笔”的独特统一性到底是啥呢?德勒兹的回答是,在一个被还原为多样性的混沌世界中,只有艺术作品的形式上的结构才能充当统一性。那么,它是怎么赋予部分和风格以统一性的呢?就是靠普鲁斯特著作里那种横向的维度,即贯穿性 (transversalité)。它确保一缕光线和一个世界向另一缕光线和另一个世界传送,确保差异之间的沟通。新的语言规则,就是指贯穿性,它贯穿语句中的内容,作品中的语句,乃至不同作品。一部艺术作品和一群受众沟通,启发了他们;或者和同一位艺术家的其他作品沟通,激发了它们;或者和其它艺术家的作品形成互通,这些都是在贯穿性的横向维度中发生的,但并没有进行总体化和统一化。【前方剧透注意】例如《追忆》中,奥黛特和盖尔芒特公爵的世界一直都互相隔绝,但在最后一部老年的他俩突然结婚,从而给这个社交界的风貌画上了讽刺性的最后一笔。【剧透警告结束】这就是时间,叙述者的维度。【其实仔细想想,时间的运行经常把一些看似不搭界的东西放在一起,给我们以神秘的启示。每次回家听到一些邻居和同学的八卦,都会让我产生这种感觉。】(169-170)
结论:疯狂的呈现与功用:蜘蛛
最后这一章探讨了普鲁斯特著作中“疯狂”这一主题的呈现、分布和作用。(171) 【感觉就是遍历和运用了前文的所有关键概念。】
首先是夏吕斯特有的疯狂,他整个人就像一团星云,其中眼睛的炯炯目光和话语中的双性特征是两颗最闪亮的星。他呈现为一个巨大的闪烁的符号,每个和他相遇的人都会觉得自己骤然面临一个有待解释的秘密,而夏吕斯本人也在不断自我解释——他具有解释的疯狂。【这段莫名有种克苏鲁的味道,一个自我解释的闪光符号……不过,具体一点的话,夏吕斯代表了一类特别复杂、结构精致的人,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身上叠加了不少历史文化的地层和社交圈子的地层。】(173)
夏吕斯这团星云中衍生出一个话语的系列,他是逻各斯的大师,以言辞优美著称。他有三种主要话语:否认,间隔和意外。套路如下:起初,夏吕斯说,“我对你没兴趣”(否认),接下来他向对方展示,“我们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但我们可以互补”(间隔),这时对话者可能会觉得挺温情脉脉,但最后,逻各斯突然偏离轨道,夏吕斯突然爆发出一阵愤怒和污言秽语的侮辱,达成了一个意外的结局。这似乎是因为,一些不自觉的疯狂和暴力的符号抵抗着夏吕斯语言的至上结构,驱逐着逻各斯、“逻辑和优美的语言”,形成了一种 pathos。夏吕斯和朱皮安(他的裁缝姘头)相遇后,语言越发解离、剥落,显露出他原本的面貌。(173-175)
逻各斯是动物,帕索斯是植物。动植物的问题之前谈太多了,我不想再展开。夏吕斯-星云似乎是《追忆》中的一个常见结构:一开始,星云在表面上构成了一个整体,但随着宇宙的演化,星云里的物质慢慢飞出去,涌入新的星云,被敞开、被解释 (unleash) 到碎片化的混沌之中,沿着一颗日渐老去的星辰及其卫星的横向逃逸线【逃逸线和 transversality 的关联】。在结尾处,曾经颇有风度的夏吕斯身材发福、声名狼藉,大腹便便地走在街头,无奈地让一些流氓乞丐缀行于后。阿尔贝蒂娜的故事也有这种结构:她慢慢从那个少女的星云中脱离,被囚禁,逃出,最后重构了原来的那个星云。
这是构成和解体的重要法则,也是爱与性的法则。夏吕斯和阿尔贝蒂娜各自代表一个同性恋的序列,先在焦虑、罪行、痛苦中解散,随后在疯狂中涌进一个跨性别的世界,在那里解体、重组成新的碎片化的个体。
夏吕斯和阿尔贝蒂娜的疯狂有几点不同:1. 夏吕斯是一个超个体化的形象,他过于有个性,从而让人困惑、想要破解,想要沟通;而阿尔贝蒂娜的问题则在于不够个体化,需要从一堆未分化的少女中辨识出她。可以说,在阿尔贝蒂娜那里,人们先看到她们小团体的沟通,然后才模模糊糊地辨认出她们本人的样子,所以,必须把她囚禁和隔离开来,予以观察。2. 夏吕斯是话语的大师,他的语言过于完美、冠冕堂皇,以至于周围的事物和客体(比如他的异样行为)都开始沉默地反对这些话语,形成偏差或矛盾;阿尔贝蒂娜则一直说着微不足道的谎言,她关心的是具体事物和客体,说起谎来没什么体系,只是临时东拉西扯地随便说点。因为她这样胡乱使用语言,所以探求语言的表面意义是徒劳的,只能通过语言的用法(包括沉默)来理解背后的深意。【这段中文极其难懂,我就按自己的理解发挥了,附英文译文:
Albertine’s relation to language, on the contrary, consists of humble lies and not of royal deviance. This is because, in her, investment remains an investment in the thing or the object that will be expressed in language itself, provided it fragments lan- guage’s deliberate signs and subjects them to the laws of lying that here insert the involuntary: then everything can happen in language (including silence) precisely because nothing happens by means of language. (178-179)
】(178) 3. 当时精神病学区分了两种符号的谵妄——解释的谵妄,属于妄想狂;要求狂(执着于追还某物)的谵妄,属于被爱幻觉 (érotomane, 翻译有问题,应该是色情狂,否则根本看不懂) 或嫉妒的类型。前者体现在夏吕斯身上,特点是他发散出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不断自我解释;后者体现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特点是叙述者一直怀疑她在私下和女人寻欢作乐。(181)
接下来德勒兹说,两人的疯狂同时对称地表现在叙述者身上。如果说夏吕斯是解释狂(不断挖掘意义),那叙述者也沉迷于解释夏吕斯;如果说阿尔贝蒂娜是色情狂和嫉妒者,叙述者的行为就更色情狂了。所以,这个叙述者与其说是叙述者,不如说是《追忆》机器中的某种配置。为了表现某种主题,叙述者会特别变换成那种样子。他是为《追忆》的各个部分量身打造的。叙述者并不具有器官,或者说,不具有他所需要的器官,而只有他所期待的器官。他整个就是一无器官身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最后,我们以一个蜘蛛的譬喻作结。如何理解无器官的身体?蜘蛛无法看到、感觉到、回忆起任何东西,它从网的一端接收到一丝最为微小颤动,于是跃向那个地点。这丝颤动,这阵波就是符号,穿透了它的身体。《追忆》形成一张蛛网,叙述者-蜘蛛盘踞在网上,每根丝都会被某种符号搅动。这蛛网-蜘蛛的组合是一部机器。叙述者不能自觉地运用任何官能,他的官能只有在符号作用于其上时,被反向激活。他身上有相应的器官,但只是一个被波激起的强度的萌芽,这个波激发了它不自觉的功用。【这很生命科学——先有刺激,再有感受器官,例如眼睛、大脑神经网络的形成。】叙述者是一个全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分泌出伸向各个角落的丝线,来创造出他的无器官身体所拥有的众多强度性的力量,以及他的疯狂展现出的众多形象。【阐释得很武断,但也很精彩。】
断断续续把这本书的笔记写完了,第二遍边写边看的过程中弄清楚了很多疑惑,产生了众多新想法,可以消化一阵子。第二部分全面发展了第一部分的主题,尤其是真理生产和跨性别、贯通性这些点。我感觉第二部分最后提出的文学机器和艺术总体性也适用于它自身——一系列彼此独立又有所联系的迷人概念,最后在一个蜘蛛的譬喻里形成了整体。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和这部德勒兹-普鲁斯特机器相连接,把它“用起来”,用它“咀嚼”周遭世界和进行创作。
我是为了一个私人项目开始看这本书的,果然不虚此行。本书对艺术创作的观点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不需要去思考作品的意义,而要让作品自己运行,或者说,作品可能只是我思维之路上的一个媒介,一种工具,重点是为自己量身打造。而当我跋涉过这条路,回头看去,或许会发现留下的思考痕迹形成了一片星云,一部作品集的雏形。
这并不是退而求其次,相反,新的艺术形式会以这种方式到来。不过,也不是说我们要刻意突破旧形式的藩篱。我想,旧形式有时候发挥了某种类似于驱迫的作用,而那些真正有想法的创作者,即使立意要写一篇最套路的小说,也会不经意间写出某种超越现有小说的东西。
下一本书还没想好,我想读《尼采与哲学》,又怕短时间内德勒兹浓度太高影响思维的营养均衡。还是顺其自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