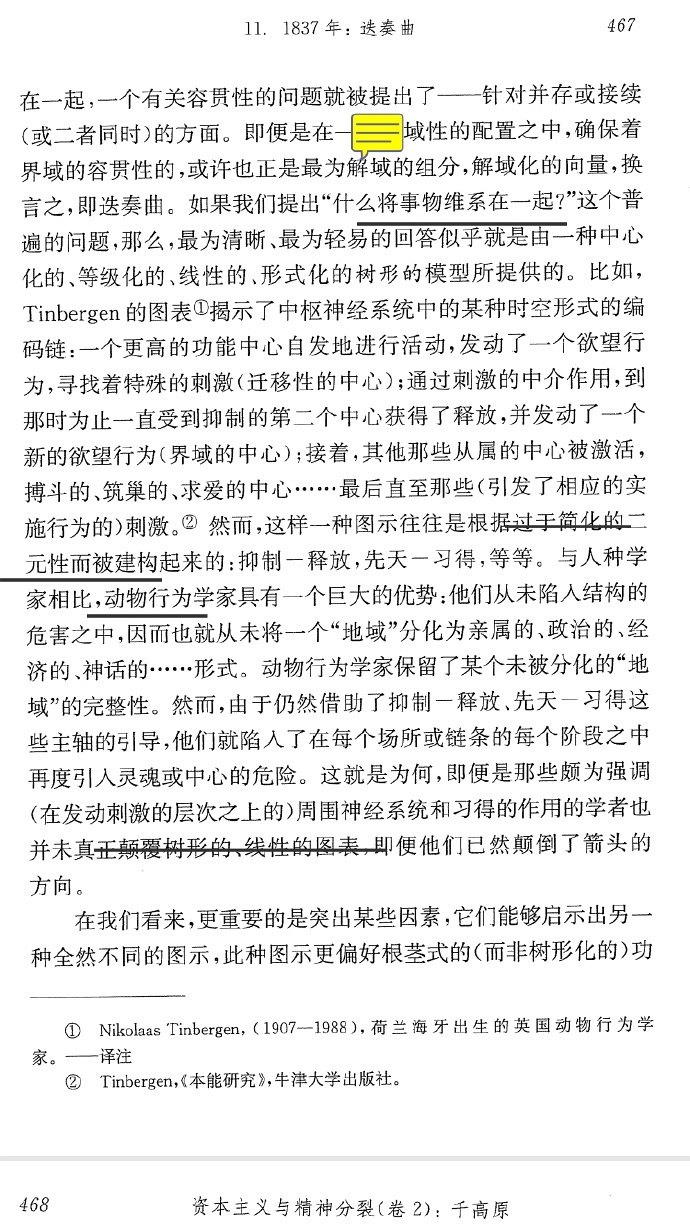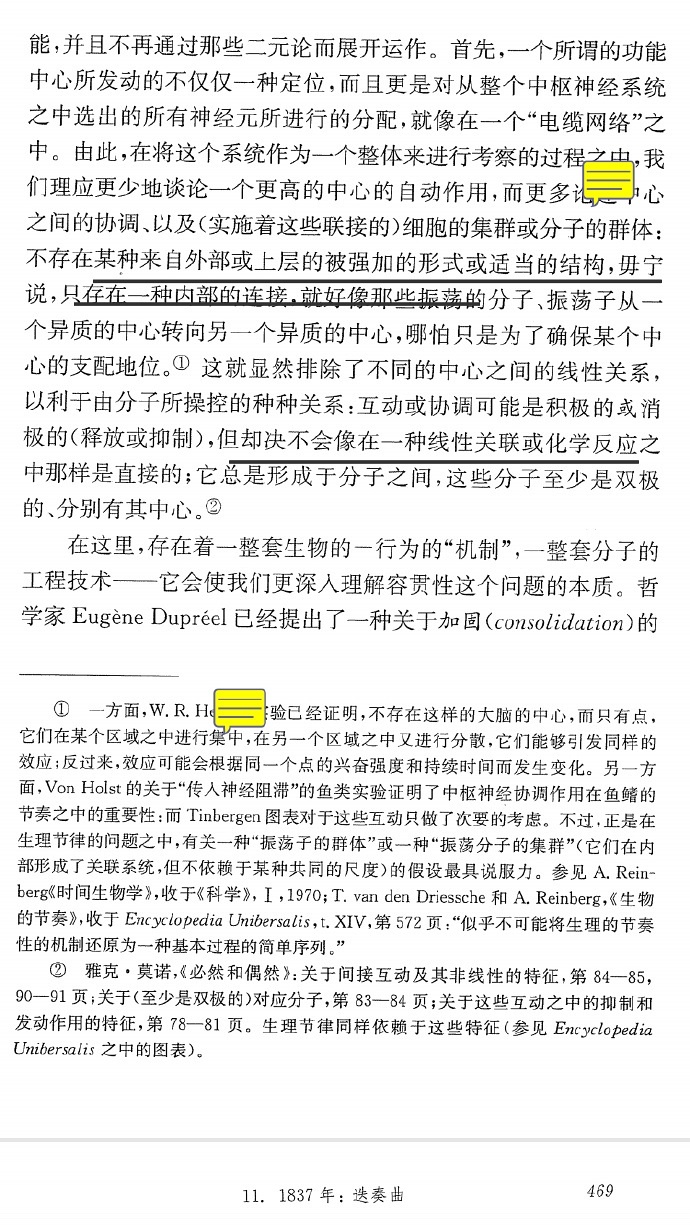“二元论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朋友对我在《反俄狄浦斯》的笔记中对二元论的强调提出了疑问,我组织了一下语言,以下是我的解释:
二元论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D&G认为二元论是必须被处理的,必须被放到根茎与多元体的视角下处理。我去复习了《千高原》序言,在17-18页的部分:“这就是为何尝试另一种相反的、但却非对称的操作是如此重要。将模仿重新联结于图样之上,将根或树重新连接于一个根茎……然而,始终应该在图样上重新定位那些绝路,以便从那里向可能的逃逸线敞开……”二元论不存在在本体论上,不存在在价值论上。(26)“我们提出一种二元论,但只是为了拒斥另一种。我们采用一种二元论作为原型,但仅仅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过程,它拒斥所有的原型。思维的矫正器每次都应该瓦解那些我们不愿形成(但却经由期间)的二元论。通过所有作为敌手的二元论(但却是完全必要的敌手,是我们不断加以变动的装置),最终达到了我们都在探寻的那个神奇的原则:多元论=一元论。”(27)
线性也完全是作为多方向的线性。是根茎线,逃逸线。不是在有一个主根的意义上线性,即可以追溯到一个“整全”的原初之根上。在《反俄狄浦斯》里当他们谈到欲望机器是二元线性的时候,他们恰恰是在反对俄狄浦斯的三角那个更有欺骗性的关系,并且二元和线性仅仅是在一种机器的属性意义上谈的(二元意味着没有一个孑然一身的匮乏主体,线性意味着打开三角的封闭,去向逃逸线开放)。
我自己为什么要强调二元论的问题,是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周围一些同学在接受了一些后现代的思想之后,他们并没有鼓足勇气去面对二元论,他们一看到二元论就好像如临大敌,转而去讨论一些所谓的“多元性”。最明显的就是在性的话题上,一谈到男女二分,就觉得不够“先进”。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之前给你看过的那个视频《母亲的艺术》,我给我的一个老师看,她是一位白人女性,对我很好,是一个物理学家。她看完之后给我的邮件里认为我在物化母亲,还认为我引用的夏尔的诗是性别歧视主义的(夏尔那句诗是这样的:“在这依然年轻的妇人体内一个男人必曾扎根于此,但他始终不可得见,就像恐惧,一直不遗余力地留在那里。”)我当时非常震惊和伤心。我给我的妈妈看过夏尔的那首诗(《要素》),我的妈妈得出的感觉是一位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战士别无选择地留下妻子和孩子走向战场。我的那位老师是一位很好的人,也是所谓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在面对这样的诗歌的时候却不能去与它一起生产自己的主体性,反而用一套所谓的“多元范畴”去审判一种情感。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样的“多元范畴”恰恰是D&G批判的那种n+1式的,用一种“进步的多元”压迫一种”落后的二元”。而那个诗人的“二元”恰恰是一种多方向的、情感的、逃逸的。
二元是黄蜂与兰花的相互生成。这是机器的二元而不是辩证法的二元。这就是我对二元的解释。
附:《千高原》中D&G关于“什么将事物维系在一起”的论述